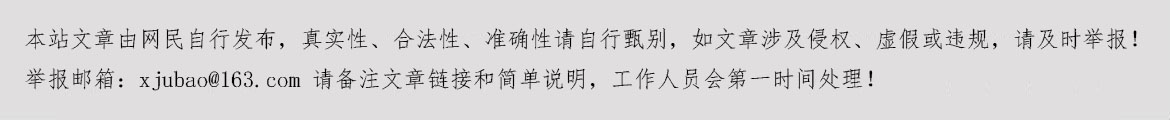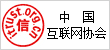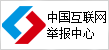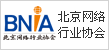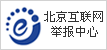林语堂,更喜欢讲“吃饭穿衣的政治”
2021-11-05 09:03:24
林语堂
假如“西式普适性”指的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拥护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人权保障,亦即新文化的“德先生”所推崇的价值,那么林语堂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上最坚定地倡导并践行此普适性的知识分子之一。
林语堂是教会学校毕业生,1916年于圣约翰大学毕业时,对西方的进步观念和生活方式早已耳濡目染。他毕业后到了北京,进入知识精英圈,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1923年从欧美留学回国时,自由民主的理念已经成为林语堂世界观的支柱。难能可贵的是,在二十世纪动荡的中国,林语堂始终践行自由民主的理念。无论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林语堂从来没有停止对独裁者批评,以捍卫人民的权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林语堂作为周氏兄弟主导的语丝社的一员初露锋芒,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对此,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已经着墨很多。林语堂自己也说,当时曾参加抗议政府的示威游行,当街向警察扔石子。鉴于其公开高调批评北洋政府,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上了黑名单,被迫离开京城,远赴厦门大学。然而,现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以鲁迅为标杆,在讨论周氏兄弟以及林语堂之间展开的所谓“费厄泼赖”之争时,过分强调了林语堂的转态。
林语堂对鲁迅提倡的政治策略确实表示附和,但其实他从未放弃过周作人在此首先提出的“公平竞争”原则。[1]在北京期间,林语堂其实一直和胡适及其他留英美派新月社成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正如陈子善在本集文中指出的,林语堂曾积极参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胡适主导的平社活动,是平社的会员。在平社组织的讨论中,林语堂曾发言指出,民主政体乃人类历史至今为止所能产生的最佳政府体制,这正是其政治取态的简要表述。
南京国民政府期间,林语堂批评的锋芒主要针对国民政府不断践踏人权的行径。他积极参与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担任领导职务,为此他曾受到死亡威胁,但他并不后悔。在他创办的中文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及参与的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中,他假借“幽默”的名义,发表了许多针砭时弊的辛辣时评杂文。有时这类文章直接拿蒋介石开涮。比如《论语》第二期,林语堂撰文《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因为蒋介石在汉口的演讲中说:
“政治这个东西,并不玄妙深奥,难懂。政治是一个很普通平常的东西,所谓家常便饭,我们随便那一个人统统能知能行的事情,甚至吃饭穿衣服,也可以叫做政治。”
林语堂评论道:
“蒋先生说空话时,我们并不佩服,倒是在此地,见出他的聪明颖慧,见识超人。蒋先生……若再多看看……《论语》半月刊,我们认为很有希望的。”[2]
钱锁桥在本集《〈吾国与吾民〉的起源和反响》一文中提到,《吾国与吾民》一书之跋题为“真实的中国”,对国民政府之腐败与无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林语堂最后决定原稿发表,是经过再三斟酌、承担了相当的风险的。
然而,正如周质平文中指出的,林语堂从来都不是一位革命性的批评家。虽然共产主义革命在现代中国影响深远、极具号召力,林语堂却是基督徒家庭出身,留学欧美,一辈子都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对共产主义从来没有动过心。何复德为本集提供了一篇精彩的讨论饮食与政治的文章,文中告诫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林语堂则更喜欢讲“吃饭穿衣的政治”,认为蒋先生如此讲还是蛮“有希望的”。三十年代共产主义吸引力上升,林语堂冷眼观之,并警告国民政府,如果政治上持续腐败下去,年轻人就会跟共产党走。
蒋介石
西式普适性是带着船坚炮利一起来到中国的,林语堂虽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但他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持续不断,这一点颇为特别。杨柳的文章讨论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正如该文揭示的,林语堂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及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联系一直都有尖锐的批评。在大学期间,林语堂就对教会学校正统的神学教条很是反感,并宣告不上教堂了,成了一位“异教徒”,但晚年在美国又宣告“回归基督教”。
其实,可以说林语堂内心一直都是一位普适性基督人文主义者,但同时一直对在华传教事业进行批评,其关键指控在于:传教事业把华人基督徒隔离于整个华人社会,制造出一批“饭桶基督徒”,还培养出自身优越感。另外,林语堂一直坚定地支持印度独立运动。在中国时林语堂便撰文表明支持印度独立的立场,后来在美国成名后,更于“二战”期间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积极参加各种声援印度独立的集会、发表演讲等,为印度独立运动呐喊。[3]
林语堂为美国的中产阶层读者阐释中国文化、人生哲理获取了文化资本,同时,他利用该文化资本来消解西方社会的东方主义偏见,特别是在“二战”期间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对西方的帝国主义进行了辛辣的批评。比如,在《东方和西方必须相会》一文中,林语堂的语气可没有以前那么温文尔雅:
“纳粹军人和日本军人都有强大的信念,而我们的战士则谈不上有什么坚定的信念,一会儿好像是说要为世界民主而战,一会儿又说要为帝国而战,有时又说是为了维持现状而战。”[4]
林语堂所说的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强大信念”当然是指纳粹德国的雅利安人主义和日本宣扬的以推翻白人至上主义为名义的军国主义。
在林语堂看来,要实现新的民主世界,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原则和信念:全世界各个种族一律平等”;西方帝国主义者必须看到“白人统治亚洲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亚洲已经觉醒了。白人的威望已经烟消云散。日本人用刺刀摧毁的东西不可能再被白人的刺刀恢复过来”。[5]现在的问题不是东西方会不会相会,因为相会是必然的,但问题是以什么方式相会。假如说在吉卜林的世界里,东西方必将以兵戎相见,林语堂则认为:“东西方必须相见,但只有当各自视彼此为君子之时才能相见。”[6]
不过林语堂对此并不乐观。《中国印度之智慧》一书有一篇很长的引言,曾在杂志上单独发表,题为《当东西方相见时》。该文与其说是在引介中国哲学,不如说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檄文。在林语堂看来,帝国主义的姿态建基于“十九世纪庸俗的理性主义”:
“科学唯物主义侵占了我们的文学和思想,已经把我们的世界搞得七零八落。现在人文学科的教授都在寻找决定人类行为的机械法则,这些‘自然法则’越被证明得井井有条,那所谓人类的自由意志就越显得是瞎扯,于是这些教授便感觉自己聪明过人、洋洋得意。”[7]
林语堂重申,他自己完全乐意看到物质进步,但科学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垄断了我们的思维,渗透到欧洲各种人文领域,让我们的现代性病得不轻。“在支零破碎的现代知识上,一种新的人文价值世界必须从头搭建,而这个世界必须由东西方携手共建。”[8]
注释:
[1]以鲁迅为标杆来讨论林语堂在此争议中的态度,可参见万平近《林语堂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年。
[2] 林语堂:《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论语》半月刊第 2 期(1932年 10 月 1 日),第 2—3页。
[3]详见钱锁桥《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以及《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8 年。
[4]Lin Yutang, “East and West Must Meet”, Survey Graphic 31 (November 1942), p. 533.
[5]Lin Yutang, “East and West Must Meet”, pp. 533-534.
[6]Lin Yutang, “East and West Must Meet”, p. 547.
[7]Lin Yutang,“When East Meets West”, Atlantic Monthly 170 (December 1942), p. 47.
[8]Lin Yutang, "When East Meets West", p. 48.
本书摘选自
塑料土工格栅 https://www.sdfclytg.com/